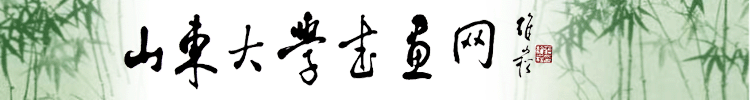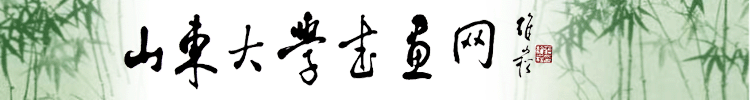蒋维崧简介
蒋维崧,别署畯,亦作骏,字峻斋,亦作畯斋,室名费白日宧、归网室,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1915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常州,2006年7月25日辞世,享年92岁。
先生生于沉涵诗书的官宦世家,可考的近二十代先祖基本都是官宦兼学者,其中明代有进士二人,清代有进士二人,直接和清代常州学派结缘。先生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并于耄耋之年被聘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顾问等职。生前为九三学社社员。
先生一生致力于古代文献和汉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尤以辞书编撰见重学林,兼擅书法、篆刻。其篆刻师从乔大壮先生,擅用金文,精于布白,参古定法,执正驭奇,以严谨、精巧、典雅著称。其书法曾得到沈尹默先生的指导,以行草擅名,远绍二王之风,人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金文则能够把古文字的学术因素同书法的艺术因素完美结合,将古老铭文写得充满时代气息和书卷气息,以其特有的风格独步当代。
先生的人生,是学问人生,也是艺术人生。
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承者,一生以人格、学问滋养艺术,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徐超简介

徐超,字逾之,斋号为三摩帝书屋、静斋等,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书法与书法文化。曾独立出版《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对联艺术》《宋诗集泉》《古代汉语语法》《大美汉字》《纸上瓣香》《介尔景福》(花笺)、《古汉字通解500例》等,二人合著《贾谊集校注》《书法教程》等。曾编译《礼记》《中庸》等文化经典,主编《九流十家》,参与编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典》、“中国文化精华文库”、《孔子文化大典》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之《书法》和《篆刻》等多部大型图书或教材。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山东《书法艺术报》特聘副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等。除曾获各类学术成果奖项外,在书法方面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二等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理论奖一等奖等。书法和书法研究得益于启功先生和蒋维崧先生,曾任蒋维崧先生工作助手多年。
目录
绪言/1
一、写作缘起/3
二、蒋维崧总论:借来“清”字说峻翁/8
三、蒋维崧研究的意义/12
四、我的书法之路与蒋维崧/19
上编 蒋维崧其人、其事/37
一、家世:沉涵诗书的官宦世家/40
二、求学:为了学问和艺术的双翼/46
三、工作经历(上):辗转十七年/52
四、工作经历(下):归队半世纪/56
五、交游:讲文论艺琴尊会/81
六、滴水知海:平生六记/102
下编 蒋维崧的书法篆刻艺术/149
一、篆刻艺术/152
二、行草书法艺术/171
三、金文书法艺术/196
四、余论/241
附录/269
附录一 本书所附蒋维崧先生临铭文书法作品释文/271
附录二 蒋维崧年表/274
附录三 徐超关于书法学科建设和蒋维崧研究的文章目录/276
后记/279
再版后记/281
序言
2003年6月,学校决定由离退休教授申报“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硕果基金”项目,项目经费用于资助出版他们晚年的学术著作。蒋维崧教授符合申报条件,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当时的社科处李红处长和我商量并经过先生同意,决定由我执笔撰写《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纳入硕果基金项目出版,并破例由我以二人名义提出申请。获批后,李红处长依例将经费使用卡送给先生。11月2日是先生89岁生日。那天晚上,在济南天外村酒店,先生将装有上述经费使用卡的信封交给了我。顿时,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我第二次感受到责任的分量——第一次是2001年我受命做他助手的时候。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后来同先生商量过,大致是想包括:(1)先生家世、生平等有关情况。(2)我对先生书法篆刻的评论。(3)先生书法篆刻作品图片。(4)其他图片,如个人生活照片、交游照片等。后来因为我连年招收博士生等工作太忙,加上多年身体状况很差,因此,除了与先生谈过几次基本设想以及零散地收集一些资料外,直到先生去世后的两年时间里,项目没有任何进展。
2008年秋天,学校实施经费管理改革:项目经费负责人必须将项目的相关信息输入个人校园卡,经费使用凭校园卡办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学校社科处批准,项目正式转至我的名下。按学校规定,项目经费用于出书,而且必须加速完成。我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拖着病躯,勉力坚持去做。虽然即使没有这个项目,“蒋维崧书法篆刻研究”也是我今后的主要任务,但它和我接受这个特定的基金项目仍然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个项目不仅是我的任务,同时也是先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是先生生前要我替他完成的任务。正当我开始全面撰写的时候,学校领导又决定将此书纳入校庆110周年重要书籍选题出版计划,显示了学校对弘扬老一辈学者学术精神的重视,这个任务因此有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下面,我对本书的写作作几点必要的说明:
1.本书力求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多地陈述事实,所以,记叙先生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和介绍他的作品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用作品说话”是先生的一贯思想,也是先生明确交代了的,所以有大量作品附图。附图同时也是我艺术评论的需要,这与一般作品集的意义不同。
2.先生本色是学者,但本书立项题目是“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故不全面论其学。
3.本书不是传记,故不用传记体。曾有人建议我写一本《蒋维崧传》,但我觉得,写传记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而我不具备;何况,本书又是原先和先生的约定,并且早已正式立项,也不能随便改动。
4.关于“其人、其事”,不求面面俱到。限于见闻,许多应该告诉读者而我又无法知道的事,自然不能写;有些事,我知道得不清楚,所以不写;有些事,先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我也没有向先生核实过,这类把握不准的事,虽然或有耳闻,也不便写;还有些事,是先生当面和我说过并有明确态度的,但这是先生和我的私议,按照他一贯的处世态度,一定不想传达给世人,所以凡属此类我也一概不写。
关于这一点,我要多说几句。从1996年开始,我每次和先生见面、谈话,都作要点记录,集腋成裘,我把它命名为《我记峻翁》,其本意完全是为了备忘。先生因此知道我凭手头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点“谈艺录”之类的东西。而实际上,在他90岁左右的时候,我还曾认真地问过他:“我写本《峻斋谈艺录》怎么样?”先生未加思考就摇头——先生摇头,其实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先生一生总是默默做事,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艺术见解,他虽然很自信,但同时也能包容他人。不过,更多的则是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认为自己的看法太不合潮流,却又极不愿意争论,所以他总是对我说“不附和,不闹腾,不争论”。虽然先生和我谈话时也十分动情,有时甚至会拍案而起,但我知道,他老人家绝不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更从不逞一时敢作敢为之勇。因此,本书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尊重先生生前一贯的处世原则,“知止有定”。——好在我已申明:本书不是传记,我更不是历史学家,将心比心,相信读者是会原谅的。
我还要特别说的是:
学门无私,学者无疆。先生作为教师,他的大门向外界敞开了数十年,弟子贤人不可胜数,而且各有时空优势、专长优势,其功成名就者亦不乏其人,想必每得亲炙,定有会心感悟处;而我则苦于生性愚钝,且对先生的了解也只限于一段有限的时空和某些层面。为了弥补缺失,本想仿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之例,博采通人,以丰富拙著内容;后来转念,想以一己之力做这么大而难的事,必有挂一漏万之讥,远不如由更多当事人亲自撰文,把更全面、更丰富、更真实的先生展现给社会。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做,从小处说,对逝者是追忆、是缅怀,对生者是激励、是教育;从大处说,记下一位德、学、艺兼备的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毕生奋斗的经历、经验,以彰其德、铭其功、传其艺,就是将一个人创造的文明成果载入中华文明的宝库,永远与世共享——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传承的一贯做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5.我长期关注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艺术成就,并发表过系列论文。这次撰写,本想对以前的成果多作些补充并改变一些写法,但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严重限制了我做事,而且项目又有时限要求,因此,我不能大动干戈、另起炉灶。我尽力做的,只能是必要的补充和修改,而其主体部分仍然是我原先发表过的一些论文。这一点,还要请读者见谅。
6.不记得是哪位前辈书家或评论家说过:评价一个书家的艺术成就,必须等他逝世五十年以后(具体多少年,记得不一定准确,但时间不短),才有望得出公允的结论。陆游更说:“后五百年言自公。”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想强调:艺术必须在摆脱人为干扰、经过历史检验以后,才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评价。这种极为冷峻严酷的理性思考提醒我,现在写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就要求我们拿出研究学问的基本态度:一无所有、冷眼旁观、实事求是。这样才有可能摒弃成见和偏见,克服时风影响和历史局限,才有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相对公允、可以得到历史承认的结论。我希望本书的基本内容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我又要说,我说“希望”,实际是想表明一种态度和愿望,并不能确保做到。其原因很多:首先,正像对一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一样,对一个人的艺术,不同的眼光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不仅是因为艺术品欣赏本就是欣赏者眼光中的“欣赏”,而且即使是同一个欣赏者面对同一件艺术品,用他不同时期的眼光看,也会有不同的评价。也就是说,不仅“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同一个观众在不同时期,看到的也可能是不同的哈姆雷特。其次,由于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的原因,以及学养、眼光、偏好、师承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我的话一定会带有认识和情感上的偏见。虽然我也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生其人、其事、其艺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如前所说,我不是写史,也不是代表什么“组织”对一个人作全面鉴定,更不用在先生“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想,无论现在或将来的什么人去评价先生,恐怕谁也不会否认他的基本人格、学问和艺术。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7.先生自然是饱学之士,但正式发表的著作不多,加上平时讲话很少,他的艺术见解多数是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从没有长篇大论的讲话,所以我们今天要系统地总结他的艺术理论,确有困难。而他和我的谈话,如前所说,多半又不便写在书里与读者分享。最好的选择,是按照先生的一贯想法,“多让事实说话”,即让读者多知道点关于他的事,多看点他的作品,从中了解他为学为艺的特点,探求他的一般审美理念和艺术取向。其实这是我由来已久的想法,并且和先生谈过多次。我说:你(我和先生向来“你”“我”相称,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都没有读“您”的音,用普通话说也很困难,先生“从俗”,不以为不敬)这几年出版的作品集价格太贵,印数又少,普通读者一般只能从报纸、杂志上了解你的书法,有些还是假的;近几年从网上看倒是方便多了,可那里也是真假难辨,所以这本书要给读者多提供些相关材料和作品图片。对此,先生深以为然。因此,我现在的做法也是当年申请项目以及后来讨论时,先生和我共同认定的。
8.我写文章往往习惯于用朴学著作的风格和笔法,实在不适合写这类书,但所谓文如其人,改也难,这就更要请读者宽容了。
2002年10月中旬,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周洁部长找到我,说学校和《光明日报》有约,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一组介绍我校杰出学者的文章,第一篇就写蒋维崧先生,并当场把任务交给我,说要求写两千字,两三天内完成。没有办法,马上就动手并按时交差,后来在当年12月5日《光明日报》刊出。查《我记峻翁》,里面有记录先生10月19日对拙文的“审查”意见:“先生满意,说‘峻翁’可用,‘清’字可用,说‘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又说:‘关键是帽子要戴得合适,有人写的文章,加在谁头上都行。’”因为此文是对先生的总括性介绍,又曾得到先生的认可,《光明日报》后来反馈也说反响很好,所以我把它作为“绪言”之二,以期读者在阅读全书前对先生有一个初步和总体的了解。
全文如下:
清,《说文》解释为“澄水之貌”,就是指水澄澈明净的样子。窃以为先生其人、其学、其艺,最合一个“清”字。兹细论之。
先说人“清”。先生年登耄耋,体貌清癯,风骨清迈,容止清雅,叙致清和。若以一字形容,非“清”而何?
进而论之,“清”由澄水之貌引申有“高洁”义,故古称高洁之士为“清人”“清士”。先生一生以道德、学问为立世之本,清虚栖心,不挠不苟,潜心读书著文、谈艺论道,俨乎渊儒硕学风范。游尘不到,清意自生,正所谓“寂士清人”也。
《礼记·孔子闲居》篇里说:“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是说圣人清静光明之德在于躬身,把“清”看成一种高尚的品德,这个“清”是清静的意思。“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庄子·刻意》)人之心,少欲则心静,心静则事简。先生清介特立,不杂交游,平时闭门扃户,隔绝尘响,一生说话很少。痛厌喧嚣,不求虚名,守静如渊,以愚自处。常有媒体找上门来为先生作“宣传”,先生总是摆手摇头;学校给他特聘教授岗位津贴他不要,有人提议设立“蒋维崧奖学金”或“蒋维崧艺术基金”,他都不同意——他不愿意以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或基金名目,而最后决定将它捐赠给书法研究中心作科研“津贴”,其“清”也如此。我同先生相识近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有高谈阔论的时候。退休以后我见他所做的事,除了读书、看报、叠纸、研墨、写字外,也就是盯着电视看看京剧、足球而已。先生就是过着这样清静、简易、平淡的生活。曾有人对先生说:“假如先生不在山东而在北京,其声名必远胜今日。”先生笑道:“声名是要付出代价的,值得吗?”皮日休《静箴》有云:“成吾高风,唯静之力。”不正是说先生嘛!
次说学“清”。讲学问而要靠上“清”字,于先生得用“清抱”“清苦”二词。“清抱”是说志趣高远,“清苦”是说功夫艰辛。先生执心清冲,矢志学问,从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在中国传统学问里浸淫七十年。七十年中,有谁知道先生曾坐过多少冷板凳,又经历过多少清苦?先生曾主持《汉语大词典》山东编写组工作达十年之久,将数十年孤月清灯下磨炼出来的治学功夫和精心爬梳的研究成果全部投入了无“产权”印记的辞条海洋中,可谓清而又清矣。
说到先生的学,还用得着“清识”一词。先生读书爱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遇到问题最喜欢查书考证,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审读《汉语大词典》时,就曾经纠正了旧辞书中的许多错误,这靠的是学者的清识、清鉴和清辨。青年人有疑难问题登门求教,先生通常是先沉吟片刻,接着匆匆走近书架,拿出一部书来,迅速翻到某卷某页,再仔细说明。有人夸奖他的学问好,他说:“我的学问在书架上。”真所谓“至宝不耀,至声无闻”,又应了那个“清”字。
再说艺“清”。窃以为先生艺术,最得一个“清”字。他的金文清峭灵动,古隶清奇古朴,行书清婉秀逸,篆刻清雅精巧;墨色清润蕴藉,章法清朗疏放。总之是气清质实,神清骨苍。先生早年爱写诗,亦多清音幽韵,连学术论文也是清言究微、娓娓道来的风格。元遗山《自题〈中州集〉后》有云:“乾坤清气得来难。”先生艺术之“清”缘何而来?答曰:缘于人,缘于学。先生本是学者,书法、篆刻,余事也;而晚年竟以“余事”名世,吾恐先生亦始料未及。先生说:“我不是职业书法家,我有我的职业,所以不受人牵制。”可知艺清首先来自心清。先生学具灵慧,高着眼光,所见者博,所取者精。上大学前,先生曾在南京拜师学画,有过“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的追求。大学期间,又选修胡小石、乔大壮二位先生文字学、书法史、书法、篆刻等课程,书法又经沈尹默先生指点,与师友潘伯鹰、李天马、曾绍杰、许伯建等人交游。此数君子皆有清流雅望,知先生艺之清亦有渊源焉。
先生为人、为学、为艺清,故与雅、静、洁、秀、正结缘,而不喜浊、俗、躁、秽、野、怪,于人亦如此。偶有俗客来访,先生往往不知所措,有时二人对视,渊默良久,直逼得对方尴尬难持,起身告退。看到电视里低级的“艺术”表演,先生则连呼“庸俗”。看书法、篆刻作品,先生最不喜浊、俗一路。他常常以人、以物为例,说:“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自残?为什么非要弄得蓬头垢面?有谁喜欢鄙陋、狂野、粗俗、丑怪?艺术品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怎么陶冶情操?”由此知先生的艺术见解竟是如此简单明了。
我经常说:与人交游如同读书。我读峻翁,观其学,观其艺,总是如坐清风,油然而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联想和慨叹。韦应物诗云:“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赠王侍御》)其先生之谓乎!
这里说的蒋维崧,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我想,如果对这类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进行全面研究,仔细考察其艺术成就与他们所走的艺术道路之间的关系,总结他们所以成功的经验,其结论对我们认识中国书法,特别是对书法教育、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都会有重要启示。我通过对先生个案的研究,觉得对于书法教育和人才培养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这就是学问的意义、沉寂的意义和人格的意义。
(一)学问的意义
首先我要说,学问和艺术没有必然联系,学问不仅不能代替艺术,甚至也不能说是成就艺术的必要条件。只是我这里的研究对象是学问家兼艺术家这样一类人,学问对他们研究的相关艺术显然具有支持或支撑的意义;同时,我这里又是说书法学科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和学问,是说书法研究人才所需要的相关知识结构,并不是倡导每个书法家都去研究学问。
其次要谈谈对书法的认识。因为只有对书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真正懂得研究书法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我没有能力说出书法的准确定义,但如就书法作品而言,书法则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主要是指笔墨、点画、线条、结体、章法等;另一部分是眼睛看不到而只能感知的,主要是指可视部分所传达出来的趣味、情感、风骨、气韵、意境,以及艺术主体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境界等。如果我们把前者理解为书法的表层结构,那么后者则可理解为书法的深层结构。其表层结构表现为躯体,即形质;其深层结构则表现为灵魂,即精神。这样说,显然有强调精神的意义,也就是强调书法本质的意义。其所以如此,乃是从艺术本质出发,对艺术的精神内涵和生命意义,以及对艺术和艺术主体的人文精神的观照,也是对艺术与艺术主体关系的根本性体现。所以我说,书法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写出来的是笔墨,是汉字,是诗文,而表现出来的却是人的趣味、情感、修养和境界。
进一步说下去:书法既然是这样一种文化艺术形态,那么,要想了解书法,就得了解与书法相关的人,以及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等等。也就是说,研究书法,不仅要研究书法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具体内容、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更要研究其赖以生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原因及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科学的书法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而所有这些研究,除了艺术学之外,还必然要求其他相关学科的直接介入;而且它们的介入,都带有根本性意义。
这么说来,这里的所谓学问,当然主要是指研究书史、书家、书迹、书体、书风、书论、书法技法和书法文化等与书法相关的必备学问。从目前全国高校和研究部门所设与书法学相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学科依附来看,除艺术学、美术学外,至少还有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字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等,而这些学科所涉及的具体学问,则大致包括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文字学、考据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学问应该也是书法学科的相关学问,甚至还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学问,因而也应该是各类书法研究人才的基本知识结构。但是,即使是人才,也不可能都是通才,所以我总是说,书法学需要多种学科的支持,拙文《启功·蒋维崧·书法人才与学科建设》(《启功先生书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书法学科建设需要多种学科支持》(《中国书法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有所论述,可以参览。重要的权威证据是,最早在中国开创书法学科建设的前辈们也都对他们深寄希望的学生说过,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问。章祖安教授1998年7月7日接受《二十世纪书法》丛刊副主编张啸东先生采访时,用很长的篇幅说到这个事情。他回忆说,当年陆维钊先生到办公室,一看见他写字就不大高兴,说:“搞在书法里头,你这个出息太小啦!”又说:“你对写字那么感兴趣干什么,到时候有做作品的时候。你不是做学问吗?赶快用心地做学问吧。”启功先生也多次对我们说:“无论是书画创作还是书画鉴定,总离不开学问。”我给先生当助手五年,关于如何指导博士生,他只说过一句话:“主要就是指导他们读书,研究学问。”而对我们文学院和山东省书协联合举办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硕士课程学习班,他的主导性意见也是“一定引导学员不要光对写字感兴趣,要逐步走‘写字—读书—作研究’的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书法教育前辈的教导,他们身体力行并以此相传的,正是他们以及他们前辈的经验总结。
社会上都说先生是书法家、篆刻家,但我想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艺术界,都会认为他首先是学问家。他矢志问学,借以安身立命者无非是“学问”二字。细心的读者都会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体会到这一点,这里先举我经历的几件事作为旁证: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可以调到南京艺术学院或南京师大书法专业任教,向他征求意见,他立即摇头反对。后来,学校有意安排我去组建艺术系(即后来的艺术学院),我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样立即摇头反对。又后来,还有一个艺术研究单位希望我去,他还是反对。在我和他一起招收书法方向博士生期间,学校有关领导曾设想我同另外几位教授组建一个招收书法等方向博士生的博士点,他仍然反对。这几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至今他那摇头反对的神情和果断的回答,清晰依旧。由此联想到他当特聘教授时“专业还是放在文学院”的表态,并说:“沙孟海先生、陆维钊先生,他们本来不是搞艺术的,只是后来被请到艺术系去了,可见他们原先的国学基础是多么重要。”他又告诉我说,他自己大学毕业后,是乔大壮先生劝他去当教师、搞学问,并说:“现在看来,我听乔先生的话就对了。”可见他立足学问的思想真是根深蒂固。——当然,他这里说的学问也主要是指与书法和书法学关系密切的传统学问。
立定学问的根基,同时又潜心于与此学问关系密切的艺术,相互发明,相互映衬,故能独放异彩,这就是古语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所以我在总结先生的艺术成就时说:“他的学问和艺术,恰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双轮。他所坚持的以学问滋养艺术、以艺术辉映学问的道路,给艺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启示。”
(二)沉寂的意义
“沉寂”是从做事的态度和方式角度说的。强调沉寂,主要出自对当前社会文化背景的考虑。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好的方面有目共睹,如新资料、各种传播手段、各种群体和活动方式、庞大的书法市场等等,这些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毋庸细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负面情形。我以为,书法界面临的最大负面背景,一是因为当今时代离传统的书法生存环境渐行渐远,客观上就为探讨传统书法的真谛带来困难;二是伴随商业浪潮汹涌而来的各种诱惑与日俱增,这些诱惑或许会使学习书法的人在兴趣之外又增加了几分动力,但也会成为书法界一切病症的根源。举例来说,许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都会经常收到各种有趣的通知、喜报甚至是“红头文件”,它们总是“慷慨”而不厌其烦地要送给你大得吓人的头衔和荣誉。“文件”上有批号,有领导人题词,有大印压底,有大腕人物参与的照片,有天花乱坠的说辞。这些“荣誉”,通常都是“大师”“院士”“教授”“博士”,以及各种“金奖”和各类“家”“长”“人物”等等,而办这些事却简单得无法再简单——就是只要掏点钱,所有你想要的头衔、职位、荣誉、证书、奖杯、勋章等立即到手,只是等级必须根据掏钱多少而定。做这些事,每个人都深知确有其“现实”意义。曾听友人说,他见过名片上印有“书法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书法之魅力竟有如此者,这就难免要“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曾在1996年《书法导报》上见到《说说书法界》一文,里面说:一年前,一位朋友看到文章作者舞文弄墨,也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就跟他要了一枝毛笔回家练字。大约过了半年光景,这位朋友便捧来了一叠获奖证书及各种邀请函,说他已被某“国际书画家协会”聘为理事等等。此后,这位朋友便列出润格表置于案头。这只是一个平常小人物的故事,但确有一叶知秋的意义。
越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越是需要沉寂。因为我们知道,传承经典文化,培养高端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健康的文化环境。但是现在,我们随处都会看到大量书事台前幕后的躁动和喧嚣,这种情势显然不利于书法人才的培养和书法学科的发展。纠正的办法就是倡导沉寂,倡导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治艺态度,倡导埋头潜心坐冷板凳的治艺方式和治艺精神,打好扎实的文化根基和技法技能根基,深入研究传统和继承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以弘扬传统、丰富传统,推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我觉得,虽然目前整治书法生存环境客观上确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如果书法界和参与书法活动的人都能沉寂下来,专心治艺,我们的书法就会有更明确、更健康的前进方向,而保持中国书法数千年来在世界艺苑中独放异彩的荣誉和地位,其希望也正在此。
总之,当我们为书法而骄傲的时候,更应该想到我们对书法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责任心,自然会沉寂做事,沉寂治艺。客观地看,老一辈学者书家在这些方面确实做出了榜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在当前形势下,他们那种沉寂的精神和品格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先生的沉寂,读本书可以体会到,下文《滴水知海:平生六记》更有集中论述,这里从略。
(三)人格的意义
人格对学问、对艺术,乃至对人生、对人类所从事的一切事业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祖国传统文化中,老祖宗总是把人格的修炼放在第一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在首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现代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并不一定与文化的发展同步,有时甚至成反比。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这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总结了人类科学文明史后,向世界人民发出的忠告。我完全相信这个忠告的正确性以及它的意义,但他的忠告比我们老祖宗不遗余力地倡导和笃行却晚了数千年。所以我以为,崇尚人格精神,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称之为精华的一部分。黄宾虹先生说:“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更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实世界所杂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周积寅、史金城编《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他这里是强调了艺术教育,但我要补充说的是,人是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人在创造各种文明的同时也修炼了自身的精神文明。所以,在一切文明遗产中,人的精神文明是最核心的文明、统帅性的文明。既然艺术是精神文明的结晶,那么艺术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这些人,更应该强调自身的人格、胸襟和气象。在这方面,前辈学者书家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曾见先生写过乔大壮先生的集联:“澄之不清,扰之不浊;难者弗避,易者弗为。”上联二句正是先生人格取向的写照,拙文《借来“清”字说峻翁》即缘此而发。下联“难者弗避,易者弗为”,又足以用来形容先生的治学治艺。我曾写《独上高楼》(发表于1999年第8期《中国书法》,刊时有删节)一文探讨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独上高楼”寓意有三:其一,先生讳维崧,别署畯,亦作骏。字峻斋,亦作畯斋。畯、骏、峻,诸字音义通,都有杰出之义。《诗经·大雅·崧高》有言:“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先生命中似乎注定要肩负起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其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王国维先生借喻问学阶段的名句。先生斋号为“归网”,取“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之意,是独上高楼的最好注脚。其三,独上高楼又是一种境界。先生灵府纯净,心无旁骛,于学于艺精益求精,难者不避,易者不为,故能独立高标,独登胜境。“导源积石源流正,维岳崧高气象尊。”陆游此语似乎专为先生其人、其艺而发,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为经典艺术和经典艺术家确立的标准和努力方向。
(四)研究先生其人、其艺给我们的启示
立身当以品行修养为要,为人之本在此。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能称之为精华和核心的理念,是中华民族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理念,也应该是当代书家立身立艺的基本理念。
立业当以相关学问、能力、修养为要,发展之本在此。任何事业都有其可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理论、知识、技术和能力,对书家特别是对书法研究工作者而言,相关学问、能力、修养是其发展之本。
立艺当以传统经典为要,创新之本在此。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创新必须以认识传统经典、弘扬传统经典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
凡治学问就必定要沉寂。沉寂亦犹面壁,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修炼,是修炼的一种形式和过程,也是成就其学、其艺的一个重要前提。
沉寂做人,沉寂问学,沉寂治艺,蒋维崧研究对我的意义在此。我想,对社会、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意义亦当在此。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社会的发展,艺术的进步,在任何时代都离不开榜样的作用,而先生应该是书法界的榜样,至少是其中的“一类”榜样。不过我还要申明:我从来不认为先生的做法就可以定于一尊,而只是认为,先生的人品、学问、艺术追求和艺术教育的方向,值得书法界研究和借鉴。
此节主要从求学经历和学术渊源角度,说明我与先生交往的原由和始末。
我把影响人生道路的基本力量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因,即个人的基本习性及个人的努力;一类是外因,即外部条件,包括关键时刻出现的人、事以及相关环境等。以上两个条件在人生各个时空阶段的相切点,形成人生道路的曲线。就我来说,简言之,我之所以走上今天的书法之路、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也是性情、志趣、师友、交游等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必然结果。其中,与书法相关的有两个重要人物:前有启功先生,后有蒋维崧先生。因为此前还有一段启蒙教育,所以这里分三段来说。
我的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时代,身边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乡贤”的文化人。她虽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因为瘫痪在床,一生不能有所作为;而因为避战乱,就常年独身住在我家,我因此成为她许多年的忘年交和“听差”。她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我所见到的最讲究生活质量的人,尤其注重精神生活,注重科学艺术,注重生活细节。她对我在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教育,以及生活艺术方面对我的影响,使我终身获益。比如,她的家人、亲戚都在上海、南京等地,我经常要根据她的口授替她写信,这使我在会写字后不久,就慢慢懂得一些尺牍常用语和写作上的起承转合。我很小的时候懂得的一点关于《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背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之类的名诗名句,也都出自她平日的讲授。印象最深的是,她家珍藏有许多装帧、印刷都非常精美的袖珍本古籍书,如《十三经》之类。书比巴掌心还要窄一点,石印,字极小,用的是极白、极细柔的宣纸。小时候看不懂,只是胡乱地翻看,但至今想起来,那时的“文化点击”依然动人心魄。我坚信它是影响我人生道路最原始、最直接的因素。
大概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从小我的字和文就常常受到褒奖,以至在初通文墨的年龄,就能帮老师批阅作文;而批阅作文必须用毛笔,写毛笔字的兴趣因此大增。待到上高中,又碰巧遇到字写得极好的两位语文老师和一位化学老师。更巧的是,这三位,一个写楷书,一个写行书,一个写行草。虽然见到的都是粉笔板书,但对我而言,已堪称“法帖”,听课总是盯着黑板随手比划。至今闭目一想,眼前还是一片洋洋洒洒的黑板白字,恰似“兴来小豁胸中气”的粉壁长廊。
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直接影响我治学方法和专业方向以至最终决定我今后数十年研究道路的,主要有两位可以称之为“大家”的老师,那就是陆宗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起初我喜欢古典文学,但后来邹晓丽先生的古代汉语课使我很快移情于文字学,开始借助于《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读《说文解字》,并进而阅读其他相关文字学著作。学习从临摹、熟悉字形开始,进而注意“六书”理论,兼及形音义的关联,由此滋生了我对文字、音韵、训诂和文献学综合研究的兴趣。在此过程中,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油印本)和《训诂浅谈》两部著作,使我粗知“章(章太炎)黄(黄侃)之学”,并在以后深深影响着我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方向。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课堂学习中断,命运却又使我认识了启功先生和他的书法。“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除顶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要接受批斗外,其他老师都可以而且必须和学生一起参加学习、开会、劳动等一切活动,学生和老师接触之多、关系之密、了解之深,都堪称空前绝后。我认识启先生和他的书法就始于此时。
学习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一是看大字报。由于他的爱新觉罗氏血统和“派曾右”的原因,启先生当时能做的也就是老老实实替“革命派”抄大字报,而他抄写的大字报在我们喜爱书法的年轻人眼里就是“法帖”。二是办板报。板报也叫宣传栏,是当时各大小单位都得办的大众宣传阵地。我是中文系专刊组成员之一,大家都把板报当报纸一样精心去办,设计版面和所刊诗文都很讲究。板报用三合板钉成,后背加龙骨。第一步是在表面裱上一层白报纸,晾干后刷上调好的浅色广告颜料,再晾干后用铅笔画线设计版面,然后用毛笔抄出各种书体的诗文。抄写时一定留下报头、边框和诗文间的空白以及所有写大标题、小标题的地方——这些要请大手笔做。大手笔者何人?就是启功先生。启先生一来,往往先是站在板报前端详一番,再看看我们的设计方案草图,马上挽袖、执笔、调色,一边审视版面一边思考,然后迅即挥笔涂抹。须臾之间,或旭日初升、长城逶迤,或山峦起伏、奇花绽放,板报顿生辉光。一时间,我们的板报俨然成了启先生的书画广告,更是全校书画爱好者观摩学习的教材。待到形势渐趋平和,人们偶尔还能见到启先生地道的书法作品,像是办在大字报区的书展。后来启功先生回忆和我们一起办板报的事情,说:“每出完这样的板报,我总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欣赏一番,观众也要啧啧称赞一番。更有有心人:前几年我在拍卖市场上居然看到我那时抄的毛主席诗词成了拍卖品,而且确实是我的真迹,价钱卖得也很好。当时有些喜欢写字的同学经常和我一起抄,我们可以相互切磋技艺。”(赵仁、章景怀编《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看到这段回忆,感到异常亲切,因为我有幸就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2002年,我回母校参加第三届汉字书法教育国际会议期间,启先生不顾90岁高龄,扶杖来到会场,正赶上我在宣读论文。一进门,他就来到我身旁坐下,我刚开口说“我们一起办黑板报……”,他马上接着说:“真是罪大恶极!”引起哄堂大笑。
通过大字报、黑板报这些媒介,前辈学者“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各种“绝招”给了我们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爱好相投的同学很快自动组合,一起学写诗填词,学古文字,学绘画、书法、篆刻等,北京市任何地方举办书画展览都会呼拥而去,一时之痴迷竟形成风气,特别是启先生的书法,得到全校师生普遍而热烈的追捧,以至“启体”竟成了“校体”。数年之后,许多同学在写诗、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都大有长进,愚钝如我者居然也略见启蒙之效,这有后来的两件事可以证明。一件事是,由于书法上粗知把笔,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前,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事部门居然派员来北师大找我谈话,说展览部缺员,希望我能去工作。后虽因故未去,却让我对书法信心大增。第二件事则发生在数十年之后,可以证明当年在篆刻方面的“成绩”:有一次我请先生指导我的一件行书作品,没想到先生首先看到落款处我的姓名印(见附图),并立即惊喜地叫道:“咦,汉印!”——这方印是我早年用破旧石料自刻的,平时很少用,更不敢拿给先生看。这次是因为手头临时没有印章才用,却得到先生的肯定,实在大出意外。我就立即问他是否能用于书法作品,先生点头,说“可用”。当然,现在看来,当年的学习基本上属于“瞎捣鼓”,和艺术还搭不上界,但对各类艺术的兴趣是养成了,多多少少也打了一点基础。
在将近八年的北师大生活经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母校情结,以及对启先生的崇敬,使我此后数十年一直关注和学习启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他的晚年还多次听他讲授文字学、书法学。他的学、行、艺不仅深深影响过北师大几代人,甚至还深深影响到全国几代人,当然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书法和书法研究。2005年6月30日启先生去世,我撰挽联二则以寄悼念和哀思:
哲星遽落,老师已去矣,耳提难忘胡人语;(启先生常常戏称自己是“胡人”,故而称他自己的话是“胡说”。)
薪火犹传,小子其勉之,手教永存坚净居。(“坚净居”是启先生斋号。)
主业典型,副业典型,因知主业昭副业;
先生师范,后生师范,幸有先生导后生。(“先生师范,后生师范”是说先生在师范大学任教,又是为师之范;我在师范大学读书,学习为师之范。)
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又有几位影响我一生的名师。首先是我的两位业师:一位是殷石臞(孟伦)先生,他与陆宗达先生同出黄门(黄侃季刚先生);一位是殷孟非(焕先)先生,他曾受教于罗常培、唐兰等名师。二位导师都十分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三大块,让我在这三个领域打下了研究基础。其次影响我研究方向的就是蒋峻斋先生。因为学术渊源和导师之间的关系(石臞先生在中央大学执教的时候,峻斋先生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而孟非先生则是比峻斋先生晚两年的同学),加上我同时也喜欢书法和书法文字学,所以很快和蒋先生认识,其影响之巨,竟使我的研究方向拐了个弯,走上了古文字书法、书法文字学以及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的研究道路,因此和书法学科结缘,这实在是我始料未及的。由此看来,我在山东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实际上只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一种继续和深化,体现了渊源有自的历史必然。
说到山东大学书法学科的发展,我们不能不说到山东大学的书法文化传统。应该说,将学术与艺术结合起来研究,是老一代学者的传统。山东大学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除先生外,童书业、黄公渚等先生都早已蜚声艺林。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山东大学逐渐形成了以文史研究为基础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风气。1980年,先生和孙坚奋教授发起成立了山东大学书画研究会,组织、联络全校爱好书画的师生,长期坚持群众性的书法创作、书法教育和书法研究活动。应该说,在后来的群众性书法活动方面,孙坚奋教授是最大的功臣。他生前一直是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又是学校书画组织的领导人。我从读研到留校任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始终是他的“麾下”,每年都要跟随他参加并参与组织许多次书法活动,直至他2004年去世。特别要说的是,1986年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增设了“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这个历史性的首创是孙坚奋教授“自编自导”、报请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的;而且在蒋先生担任首任导师期间,孙坚奋教授也参与了部分指导工作。此外,早在1996年,王长水教授就发起成立了东方书画院,并在那里招收了第一届外国来华主攻书法方向的硕士生,这在山东大学也是一个突破。
下面专谈我与蒋先生的事。
我和先生的交往大致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从我研究生入学的1978年到1995年,约十八年;后期是从1996年到2006年先生去世,约十年。交往所谈,前期以纯学术如文字、音韵、训诂、古籍整理等为主,兼及书法;后期则相反,主要谈书法、书法文字学和学科建设。
前面说过,早在1986年,先生开始在中文系“文字学(含书法)”方向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这件事奠定了山东大学书法学科建设的基础。但在先生1987年退休以后,这个方向就一直没有招生。直到1996年,学校决定让我从文字训诂学研究方向转至这个方向继续招生。因为先生是在这个方向招生的唯一一位导师,现在我要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从事他的事业,这客观上也就决定了我和先生势必要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招生前我向先生请求:我要定期到先生家里向先生请教指导书法研究生的一些问题。我一开口,先生就爽快答应。从那以后,我就订了长期学习计划。虽然计划有时中断,但总共算起来却有十年之久。
2001年1月8日,我被批准为新任博士生导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后,他很高兴。后来学校执行特殊人才计划,先生应聘为特聘教授,并确定为中文系博士生导师。8月,我和先生确定了二人联名招生、联名培养博士生的方案,并经过学校批准于第二年招生。后来,学校又确定我做先生的助手,全面协助他的工作。种种因素和条件结合在一起,使我更能名正言顺地为他多做事、向他多学习。就这样,我以这种身份在先生身边工作了五年,直至他2006年7月去世止。
先生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还特别关心组建书法研究中心,对中心的人员组成、课题任务乃至经费等问题都作了明确指导,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关于这些,我在为山东大学书法研究中心“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丛书”所写的“前言”里,对先生支持出版学术著作表达了永久的感谢。
关于我向先生请益及与其交往等具体情况,下文都有详述,这里不赘。
九州君子宇,数仞圣人墙。先生沾溉后学多少,难以言说。2000年秋天,我曾临金文一篇,下附数语云:“我学金文,有幸亲炙于常州蒋峻斋先生。然愚以为亲炙之益,不在克隆之便,而在大圣现前,芳轨不远也。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生细审后含笑称是。今日思之,仿佛如昨,不禁黯然神伤。教泽长随河海远,艺才恰似泰山高。相信薪火可传,视学问、艺术为第一生命的真学问家、艺术家,一定会从先生的治学治艺道路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继续其未竟的事业。